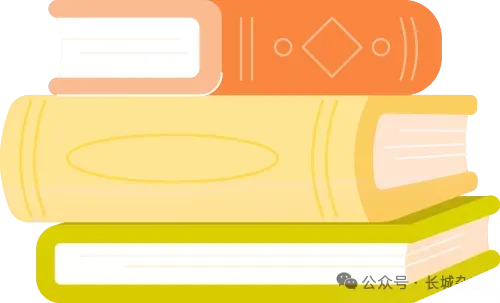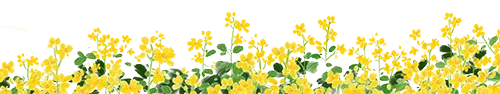《烟台日报》·散文 | 张凤英:母亲是一本无字的书
- 2026-02-06 22:25:14

图片来自网络
母亲是一本无字的书
张凤英
夜深人静时,我常会从书架上取下那本纸页泛黄的《红岩》。它安静地立在光影里,薄薄的一册,却沉得让我这72岁的手微微一坠。封面上江姐的形象已有些模糊,书脊的线也有些松了,像一位疲惫却依旧挺直腰杆的老友。我摩挲着它,粗糙的触感从指尖传来,忽然觉得,这哪里只是一本书,分明是母亲那只同样粗糙、带着凉意的手。
那时家中的光景,是浸在一种青灰的底色里的。全家九口人,全靠父亲每月六十七块八的工资撑着。社区的黑板报上,白粉笔清清楚楚地写着:人均(月收入)不足十元,即为贫困户。我们家,恰恰就在这“不足”的线上沉沉地挂着。因此,每年春节前,我们总能领到一笔国家发放的救济金。父亲接过薄薄的信封时总是垂着眼,手指捏得紧紧的,仿佛那纸张有千斤重。那钱是用来割几斤肥肉,给年夜饭添点油星的,或是给我们姊妹扯上几尺布,缝制成开春的衣裳的。每一分钱,都在母亲的心里被掰成了几十瓣,算计着落处。
可偏偏我迷上了书。学校阅览室里那几本被翻烂了的连环画,早已满足不了我心里那头日渐饥渴的幼兽的要求。我想要的,是那些厚厚的、散发着油墨香的“字书”。那欲望是奢侈的,甚至带着点可耻,尤其是在弟弟妹妹的鞋底又磨出了洞、晚饭的粥碗照得见更清晰的人影时。但我还是说了,声音怯怯的,像蚊子哼一样。我说,想要一本《红岩》。
母亲正在灶台边舀水,手里的大瓢顿了一下,水声哗啦,格外响。她没回头,只问:“多少钱?”
“一块……一块两毛八。”
我报出这个数字,自己先被它扎了一下。一块两毛八,能买多少斤盐、多少支铅笔啊。
母亲再没说话。锅里熬着的野菜粥咕嘟咕嘟地响,那声音吸走了屋里所有的声响,也吸走了我方才那一点点勇气。我低下头,准备让这个念头像以前的许多个念头一样,无声无息地沉到心底去。
然而,第二天放学,我刚进门,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方方正正的东西。我心头猛地一跳。母亲从里屋出来,在围裙上擦了擦手,声音平平的:“书,给你买回来了。”
我不敢相信,扑过去,三两下扯开报纸。果然是《红岩》,崭新的封面,红色的书名像一簇小火苗,瞬间烫红了我的眼睛。我猛地抬头看母亲,她已转身去收拾灶台,只留给我一个习以为常的、忙碌的背影。
后来,我从妹妹嘴里零星听来了母亲买书的经过。原来那天,母亲拎着一个小竹篮去了集市。篮子里是家里攒了不知多久的十几个蛋。平日里,这些蛋是家里的“银行”,弟弟头疼脑热时换几粒药片,灶头的盐罐见底时换半包粗盐。那天,母亲在集市的人流里站了大半晌,小心地将蛋一个个递给挑剔的买主,换回一把毛票。
那时的我,全然不懂那一块两毛八里,浸着多少个本该属于全家的、热乎乎的清晨。我只顾着狂喜,一头扎进那本书的世界。江姐的坚毅、许云峰的智慧、小萝卜头的天真与不幸……那些铅字像有了生命,在我眼前奔腾呼啸。我读了一遍又一遍,总共读了十几遍,许多滚烫的段落,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。澎湃的心潮无处安放,便化作笔下的文字——一篇长长的读后感。没想到,这篇稚嫩的文章,竟被选去区里的少年宫展出了。
我得意地将这个消息告诉母亲,指望从她终日平静的脸上看到一些波澜,一些为我骄傲的闪亮。母亲正在纳鞋底,针锥在头皮上轻轻擦过,引着麻线穿过厚厚的布层,发出“哧啦”的、结实的声音。她听了,只是抬起头,极淡地笑了笑,说:“能展出去,挺好。”那笑容短得像夏夜的闪电,还没让人看清温度,便隐没了。随即她又低下头,专注于手中的活计,仿佛我刚才说的,不过是“今天天气不错”之类的闲话。我心里那点膨胀的得意,像被细针戳破的气球,噗地一声,悄无声息地瘪了下去,转而有些莫名的委屈。
许多许多年后,当我也历经了生活的磋磨,懂得了沉默背后可能扛着多重的山峦时,我才在某个瞬间,忽然读懂了母亲那短促一笑里的全部内容。那不是淡漠,而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,在竭尽所能地为我挪开一方通往“有字”世界的障碍后,看到女儿真的跌跌撞撞地跑了进去,并且似乎还跑得不错时,一种如释重负的、几乎不敢表露的欣慰。她无法用“理想”“信仰”这样的词汇来鼓励我,只能用最实在的行动——卖掉鸡蛋,换回书本——来为我铺路。她的欣慰,不在于那篇文章被展出,而在于她换回的那些“字”,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作用。她的爱,从不说出,只默默兑现。
母亲去世多年了。她的一生,仿佛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“兑现”瞬间连缀而成:将褪色的旧衣兑现成我们身上的整洁,将粗粝的粮食兑现成我们碗中的温热,将她全部昏暗的、没有“字”的人生,兑现成我们眼前逐渐开阔的、有光亮的道路。
如今,我的书房四壁皆书,华灯粲然。我拥有了母亲当年无法想象的一片“字”的海洋。可我最珍视的,仍是这本《红岩》。它不仅仅是一个革命故事,而是我人生的第一份“信用证”,是母亲用最朴素的“抵押”,为我换来的通往广阔世界的唯一通行证。封底那个模糊的用铅笔写的价码“1.28元”,在我看来,是天下最昂贵的数字。它由十几个鸡蛋、母亲半晌的站立与无数的沉默构成;它利滚利、息生息地,让我用了一生去偿还,却愈还愈觉得亏欠。
窗外,城市的光流无声地闪烁,那是一个由无数璀璨的“字码”构成的世界。我翻开书页,再一次读到江姐就义前的那段话。字迹已有些模糊,但我无需看清,那些句子早已刻在心里。恍惚间,那铅字的行列微微晃动、变形,化作了母亲当年在灶火前、在灯下,那一个个永恒沉默的侧影。原来,母亲才是我一生中读到的,最厚重、最沉默、却每一个“字”都是用生命铸成的书。这本书没有封面,没有页码,却写尽了爱的所有释义。而我用尽一生,也不过刚刚读懂了它的序言。

2026年1月30日《烟台日报》刊发版面